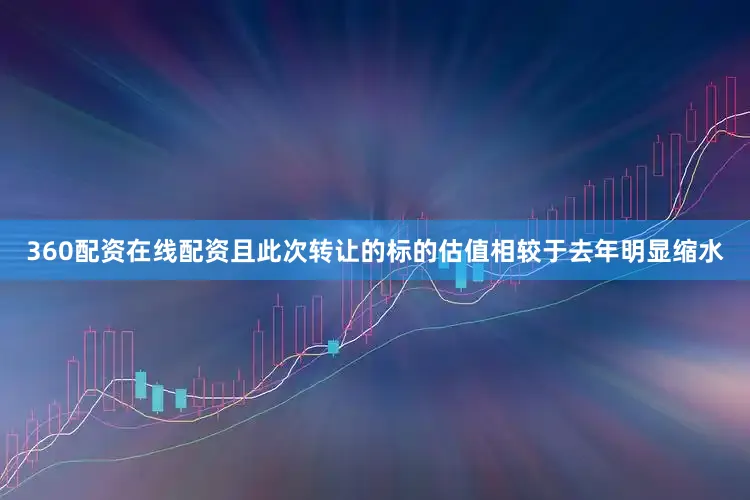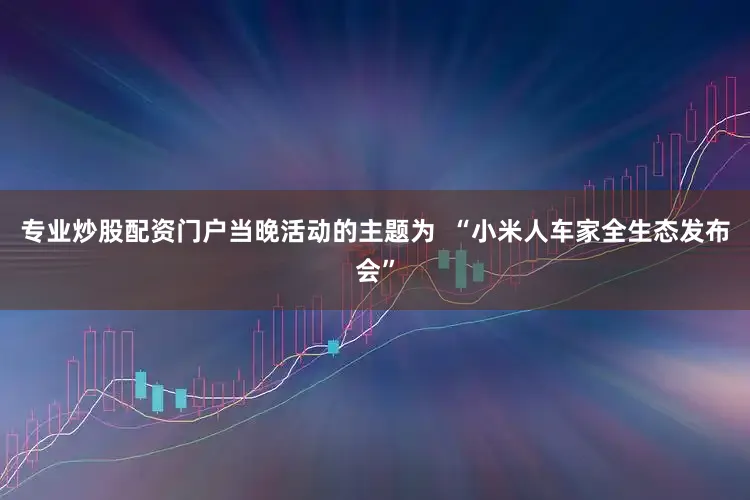中国革命摄影先驱沙飞。
《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》
(1938年,沙飞摄于河北浮图峪)
《鲁迅(左一)与青年木刻家》。
(1936年,沙飞摄于上海)
展开剩余80%《打谷场上》
(1943年,郑景康摄于延安南泥湾)
“哪里在燃烧,就去哪里拍摄!”这是战地摄影界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。
抗战期间,无数中国摄影家以相机为武器,冒着枪林弹雨,用生命践行这一句庄重的誓言。他们用镜头将硝烟弥漫的十四年抗战史永恒定格,构筑起中华民族苦难与抗争不可磨灭的“视觉史诗”。
这支特殊的队伍里不乏广东摄影家的身影。沙飞,就是其中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。他如同自己的笔名一样,像一粒沙子在抗战的硝烟中飞舞,拍摄了《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》《115师挺进平型关》等大量反映军民抗战的珍贵照片。
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,石少华、郑景康、赵烈等广东籍摄影家也纷纷拿起相机作为武器,留下一幅幅黑白无声的历史证词。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再度翻开斑驳的历史相册,那段凝固在影像里的峥嵘岁月又一次浮现在世人眼前。
●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本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宣传抗战“最有力的武器”
硝烟弥漫的1938年,河北涞源县浮图峪古长城上,八路军机枪手俯卧在茂密的草丛中,手持驳壳枪的指挥员严阵以待,警惕地注视着前方,他们威武的身影与蜿蜒的古长城融为一体,宛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座丰碑。
这幅由摄影家沙飞拍摄的《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》,已成为铭刻在国人记忆之中的经典之作,它同样深深地触动着广东省文联副主席、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李洁军。李洁军表示:“沙飞的摄影作品有着很强的象征性。长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符号,他善用长城作为八路军抗击敌寇的背景,成为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诠释。”
沙飞,原名司徒传,来自广东开平。“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,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。”沙飞是他为自己所起的笔名,也正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真实写照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他毅然离乡北上,成为八路军首位专职摄影记者。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,从晋察冀反扫荡到大反攻,沙飞始终穿梭在抗日最前线,用镜头记录无数军民英勇奋战的珍贵瞬间。
沙飞的现代文艺观受到了鲁迅等人的影响与熏陶,他也因偶然的机会拍摄鲁迅先生最后的公开活动而一举成名。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蔡涛介绍,新兴木刻运动先驱李桦,以及同为开平司徒家族的两位艺术家——画家司徒乔与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,“他们用艺术改造社会的努力,也推动着沙飞摄影观念的转型”。
“一张好的照片胜过一篇文章。”正如郭沫若所言,沙飞同样清醒地意识到,在文盲率高达八成以上的旧中国,相较于文字或其他造型艺术形式,摄影在唤醒民众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,自然成为“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”。
早在1936年,为了揭露日本人潜入我国边防海岛秘密活动的阴谋,沙飞将自己在汕头南澳岛拍摄的照片重新编辑,并以《南澳岛——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》为题在《生活星期刊》上刊登,成为“国防摄影”的经典之作。“此时抗战尚未全面爆发,沙飞就注意到:敌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勘察地形了。”沙飞的孙子王平说。
沙飞不但用镜头记录战争的残酷,同样善于捕捉人性的温情。百团大战胜利后,八路军战士发现并救助了一对日本小姊妹。她们在晋察冀根据地总部还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悉心照料,闻讯而来的沙飞将这感人一幕定格,留下《将军与孤女》系列照片。三十多年后,这组照片重见天日,还促成孤女美穗子与聂荣臻元帅重逢的一段佳话。
时至今日,《将军与孤女》《白求恩在晋察冀》《扛着木制机关枪的儿童团》等经典之作依然脍炙人口,闪烁着中国人民人道主义的不朽光辉。
构建“人民视角”的战争记忆
“沙飞对中国摄影有三大贡献:创办《晋察冀画报》、提出‘摄影武器论’、培养一批红色摄影战士。”回顾沙飞的抗战历程,李洁军如此评价这位先驱者的功绩。
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,八路军手里的每一卷胶片、每一台相机、每一滴显影药水,甚至每一份制版印刷纸张,都需要从敌占区冒险运送而来。然而,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抗日根据地第一份纸质画报——《晋察冀画报》,于1942年7月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创刊。
《晋察冀画报》不仅在延安等国内革命根据地发行,更向世界打开了传递中国抗战声音的“窗口”,在中国新闻史上树起了一座“红色坐标”。仅在晋察冀边区,报社就先后举办摄影展300余次,向其他根据地、国统区和外国发稿多达5万余张,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。
在战火中保存底片困难重重,坚守岗位往往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1943年,在日军一次突袭中,晋察冀画报社政治指导员、广东籍摄影家赵烈为营救战友不幸牺牲,年仅23岁。“人在底片在!”赵烈牺牲前发出的豪言壮语仍在国人心头回响。
更多广东籍摄影家继续沿着沙飞的足迹前行。香港出生的石少华也是“摄影武器论”的积极践行者。担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期间,他拍摄了大量反映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雁翎队等经典题材的战地照片。《白洋淀上的雁翎队》是他六进六出白洋淀,充分体察水上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后精心构思拍摄而成。
抗战爆发后,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之子中山籍摄影家郑景康,也从香港北上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“一粒枪弹只能杀死一个人的肉体,一幅有力的照片可以转移多数人的成见,感动无数人的灵魂。”在延安期间,他拍摄《陕北与江南》《南泥湾之秋》《兄妹开荒》等大量反映根据地军队革命斗争和大生产运动的照片,作品获得毛泽东“能抓住动态”的肯定。
据统计,在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中,来自广东的摄影家就超过四成。“广东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,能在抗战期间产生如此庞大的摄影家队伍并非偶然。”李洁军认为,技术与理想的交融使广东摄影家得风气之先,他们还打破了传统战争摄影的英雄叙事模式,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视觉语言:以直接、质朴平视角度的构图,自然光条件下高对比度的效果,共同构建出“人民视角”的战争记忆。
在沙飞、石少华开办的摄影训练队培养下,晋察冀边区的摄影队伍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,从最初仅有沙飞一人,发展到后来上百人的专业队伍,其中流萤、袁克忠、孟庆彪、杨振亚、宋克章、袁苓、李峰等名家,都成为日后新中国摄影事业的中坚。
八十年光阴荏苒,这些珍贵的抗战摄影底片,不仅守护着历史记忆,更锻造着民族精神。“它们所蕴含的精神力量,至今仍为讲好‘中国故事’提供着宝贵的启示。”李洁军总结道。
发布于:广东省宏泰配资-炒股配资咨询-最新配资平台-券商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配资合法吗用镜头光影抒写家国情怀
- 下一篇:股票配资炒备受期待的男单决赛如期而至